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谢泳曾以1918年山西疫情为例,证明85年前阎锡山政府对于肺鼠疫的预防工作,卓有成效。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虽然蔓延28县,导致2667人死亡,但是,疫情在蔓延74天后,即被扑灭。谢泳依据的史料源自疫后所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叙述疫情如何蔓延,第二编记载防疫行政如何展开,第三编收录与防疫有关的电文、法令和演讲稿。三编合计690页。承蒙谢泳寄赠所藏该书之第一、第二两编,笔者又在上海图书馆觅得该书,将第三编复印携归,并将第一编中的若干缺损页面予以补印。细读过后,觉得有必要对于此次疫情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项研究以1918年的肺鼠疫为中心,却不以之为全部。这是因为,关于民国时期的山西鼠疫记载,还有另外一些资料来源。其一,当时的医生留下一批珍贵的出诊报告。其二,当时各种报纸的相关报导。其三,1960年代新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展开对于历史时期山西鼠疫流行史的调查。只不过,其中有关1918年疫情,皆转引自《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比照各种文献进行阅读,有一个细节颇令人不解:1918年年初山西省的肺鼠疫大流行,没有波及晋西地区的临县和兴县,然是年秋天临县死于腺鼠疫者,多达181人,兴县疫死8人。实际上,在1918年以前,临县、兴县就多次发生疫情,每次死亡人口分别为数人乃至数百人。从1918年至1942年,临县、兴县每年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染鼠疫身亡。例如,1924年临县就曾疫死959人,兴县疫死170人;1931年临县疫死1198人,兴县疫死967人。相对于1918年的肺鼠疫流行,临县和兴县的“疫后之疫”不能说不严重,人口死亡不能说不多。按照1918年的政府动员能力,要消灭或遏止临县的鼠疫流行,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自1918年春天以后,那个曾经展现其高度动员能力的政府不复存在。原因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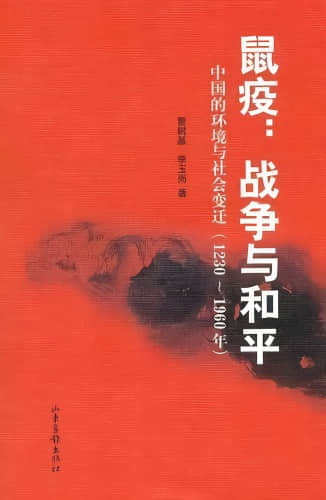
是不是由于1918年春天结束以后,山西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政府权力的弱化,从而使得政府的防疫职能,不是加强,而是缩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于民国时期山西地方政治史作一简单的回顾。
民国时期的山西政治,与阎锡山密不可分。1916年7月,阎锡山任山西督军。1917年9月兼任省长,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1918年1月至3月的肺鼠疫大流行,即发生在阎锡山掌控山西军政大权的三个月以后。
1918年4月,即肺鼠疫被扑灭以后,阎锡山在政治上推行“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在经济上推行水利、蚕桑、植树、禁烟、种棉、造林和畜牧。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1924-1927年,阎锡山率部参加的北伐战争以及其他战争,主要发生在山西境外及山西边界,对山西本土无大影响。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以后,阎锡山虽然隐居,却在实际上掌控全省大权。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任太原绥靖主任,从台后走上台前。阎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山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这一过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山西才被中断。
据此可知,临县、兴县等地的“疫后之疫”,与山西地方政府权力变化无关。为此,对于上述怪异现象,必须寻找新的解释。
1918年的全民防疫
1918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接中央急电,告知归绥属境五原发生肺型鼠疫。1月4日,段祺瑞政府之外交、内务、交通三部联合致电山西省政府,称美国医生认为五原一带的时疫可能为肺鼠疫。各国外交使团又称归绥距北京交通便捷,应当严行防止疫情传入。所以,派伍连德医官专司其事,请山西沿途官吏协助云云。伍连德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鼠疫防治专家,曾组织扑灭1910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北洋政府派伍连德前往五原一带视察疫情,也有将疫情当作鼠疫的基本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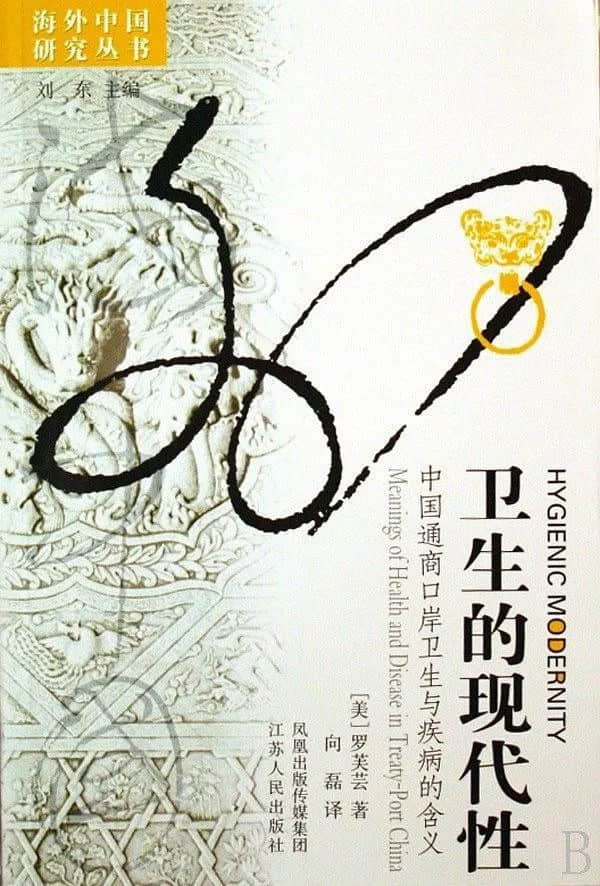
1917年8月,肺鼠疫首先在扒子补隆—教堂爆发流行,死亡约70余人,群众恐慌,四散投亲奔友,致使肺鼠疫沿途向东南传播。扒子补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梁素海西岸,现名新安镇,当时属于五原县辖。9月下旬,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将疫情向外迅速传播。9月下旬传入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到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卓资、丰镇等地,进而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东、安徽、南京等省市,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
1918年1月5日,山西省之疫情首先在右玉县爆发。右玉地处绥远与山西交通之要道,最初的死者是2名南下的旅客。阎锡山迅速报告中央。山西防疫全面展开。
军事动员
1月5日,山西军政当局下令“遮断交通,严密检查,则南下行旅不可复返”。省军署迅速组成防疫办公处,调动军队迅速建起防疫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北(外)长城为界,自阳高县天镇为起点,沿长城直至河曲县,折而南下,沿黄河至临县碛口。作为以后腺鼠疫流行中心的临县也包括在防线之内。
第二道防线以南(内)长城为界,自灵邱经繁峙雁门边墙以北各县,经宁武、苛岚,至兴县黑峪口,与陕西隔黄河相望。作为腺鼠疫流行中心的兴县包括在防线之内。临县位于兴县之南,也在第二道防线之内。
第三道防线,自雁门关以南,东至五台,至与直隶接壤处,西至临县与陕接界处。临县碛口,成为第一条和第三条防线的交汇处,全县处于三条防线的严密保护之下。

在第一道防线,长城横亘七百余里,其间隘口众多,南向沿黄河有大小渡口。合而计之,第一防线较大的关隘渡口54个,小者不胜计算。军队将小口概行遮断,只在得胜、杀虎等八口施行检查。第二防线,设定雁门关北广武镇、关南阳明堡等十口施行检查,其余遮断。第三道防线设置于代县、忻县陷落之后。合而计之,军队驻防的关隘渡口为48处。驻防的军队有第一混成团二营、三营、步三团二营、三营、步五团二营,骑一团、骑二团,第二混成旅司令部、第三旅、第四旅、宪兵二营和防疫分队。1918年的防疫,对于山西的军人来说,不啻是一场战争。
军队藉其武力成为遮断交通的主要力量。1918年1月,时值旧历岁尾,俗称腊月。山西境内在关外打工者和经商者,春出冬返,岁以为常。每年年关,由北而南的大道小路上,人潮汹涌。岁末寒冬,断绝交通,即断绝晋人回乡之路。没有军队的弹压,实在是不可想象。
1月25日,阎锡山电致交通部:“已飞电大同镇道及阳高县知事派遣军警,驻小屯口,杜绝阳高与丰镇之行人往来,以绝疫氛。”说的是雁北地区阳高县与丰镇县之交通阻隔。同日,阎锡山又致电内务部:“晋陕交界已饬各营县断绝交通,并转知杨医士矣。”说的是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的交通阻绝。2月14日,阎锡山致电内务部,电告广灵县发生疫情,故断绝山西、直隶两省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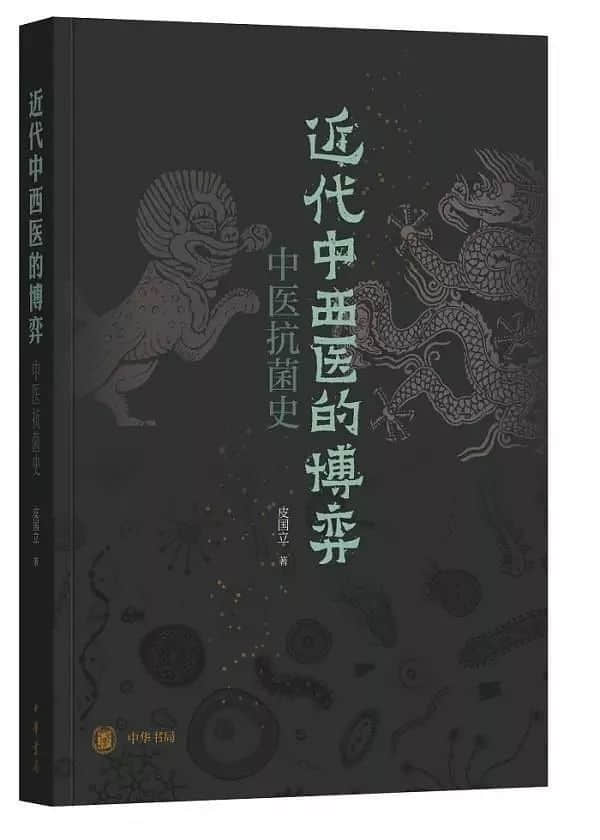
对于山西省的交通而言,军队人数有限,不敷分派。阎锡山动用警察力量,一并投入交通阻绝。所谓“以陆军为经,专注重于三大防线,警察为纬,专致力于县境冲途。更由各县区推而至于村镇,由村镇而里巷”。由于及时有效的军事动员,使得阎锡山在控制疫情传播方面,基本掌握了主动。疫情的控制也卓有成效。
行政动员
在医疗行政方面,山西省政府召集省城各医院以及军警机关所有的西医医生及曾留学东洋或西洋之医生,“无不优礼致之,派往各地担任检查”。北洋政府之内务部介绍美籍医生杨怀德莅晋,被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根据统计,参加防疫工作的中外医生及看护员共有67名,其中有36个医士(包括一名医学博士)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他们分别派往代县、宁武、偏寨、五关等各防线所经之县,构成防疫的主要技术力量。
这批西医在各冲要路口承担起检疫的重任。“沿边各口凡属北来行旅,须经医士诊断色脉形象,确无疫症者收入留验所,其有身体不甚康健稍涉疑似者,则送入隔离所”。“于车辆初到时,查明系来自疫地或从疫地经过者,立时由医官消毒,指派警士交由检疫所留验”。
担任防疫工作的西医还活跃于各疫点村镇。2月2日,崞县知事向阎锡山报告:轩岗镇天主堂长带领该区疫村人至镇,为村兵所阻,“彼时叶、魏二大夫正在该镇检查,声言须请示上宪惩办”,“又报叶、魏二大夫已到宽滩、神山堡等村检查,据称宽滩似可无虑,神山须一星期后才能扑灭”。《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所载第五类文件为《报告》,其中第一项为《西医报告》,记载有从1月24日至3月30日驻扎各地之西医关于疫情的报告。总之,在山西省的防疫工作中,西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行政组织方面,省一级的防疫的机构有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省防疫总局和晋北防疫事务所。阎锡山任督军兼省长,因此,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和省防疫总局,其实都在阎一人领导之下。各种机构的设置与功能相当繁杂,兹不赘述。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收入的大量电报可以证明大疫期间政府行政的严格与效率。兹就其简短者转引如下。
1月28日,阎锡山电保德知事:
原平镇早已严加防堵,李世方、李世荣等何以得此疫症,系由何处染来,应速查覆。
2月1日,阎锡山电应县知事:
据调查报告,该县东关及贾寨、黄尾子、剪子铺等处,瘟疫甚烈,剪子铺死八九人,即弃尸野外,黄尾子死一人,亦四五日无人掩埋等语,此事关系多数生命,该知事何竟毫不过问,以致传染日烈,实属玩视民命,著先记大过二次,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严办。
从类似电报中还可知,代县曾知事宝豫办理不力,被“撤任示儆”。处理决定通报国务院、陆军部、外交部、内政部和交通部。右玉县知事因未及时报告疫情,被记过一次。大同镇道警佐沈寿飏“有溺职守”,阎饬令警务处“撤差惩戒”。
防疫中最严重的疏漏莫过于分水岭事件。腊月二十三四日,有受雇于省北疫区的脚夫张学儿,从祁县前往沁县购米,回程时路经武乡分水岭一客店,将疫情传开。阎锡山为此给清徐、太谷、平定、祁县、沁县、定襄、浑源、宁武、长子、屯留、长治、辽县、榆社等十三县知事拍发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文,通告武乡县知事被撤职一事,并令其在新任知未到任之前,“仍应振作精神,迅速图功。如再因循,定即拿解来省严予惩办”。不仅如此,2月18日,还有一份电报拍给忻县警佐,电文称:
据报该县东区之董村警察分所私放商旅通过。本署派员李海清在石槽卡曾见有北来脚夫持有该分所图记等情,仰速查禁,并切究该分所有无通贿之弊。
上述两例可证:防疫无小事。这是因为,防疫过程中的任何失误,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毁灭性的。1918年的山西防疫,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
民众动员
疫事初起,阎锡山即根据西医之说,确定鼠疫为“有防无治”。在通令全省遮断交通的同时,“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并聘请各国医生、牧师、教士分投帮助,派委宣讲多员,乘机利导,其注重之点,在使人自防卫,家自引避,村自隔绝。忍一时之痛苦,保万姓之安全”。1月21日,阎锡山致全省文武长官,详细告知肺鼠疫流行机理。整个电文不足500字,却详细阐明肺鼠疫之传染途径和潜伏期,病人如何使用口罩,污物如何处理,病死之人的住房如何消毒,病人、病家和疫村如何隔离等。在肺鼠疫流行病学的知识普及方面,山西省各级官页与普通民众一样,也需要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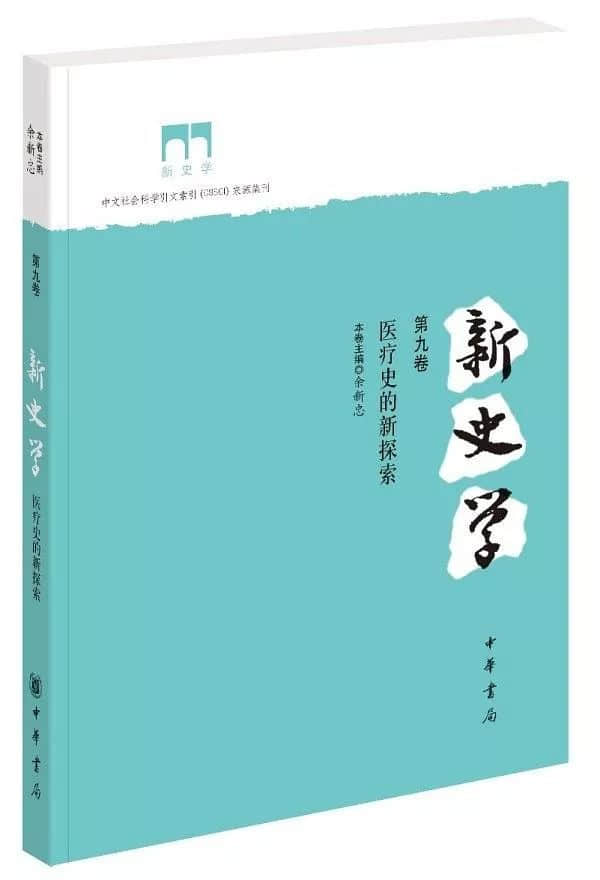
疫事初起,北洋政府内务部即嘱山西省政府须将防疫一事,布告于民。于是,山西省防疫总局专设防疫讲习所,并于各县专设防疫宣讲员,组织防疫会,并“刊布白话布告多种,电饬各知事随时晓谕”。在一些地方,宣讲员深入村庄进行宣讲。1月25日,阎锡山电告一二防线内各县知事:
本署已派宣讲员携带公文前往该县办理宣讲防疫方法,俾人民均有普通防疫智识。应由该知事先分路选定防疫宣讲员二十人以至六十人,俟该宣讲员到时,即先讲明防疫办法,以便分赴各村宣讲。
由省署派出的宣讲员是省级宣讲员,由县知事组织的宣讲员是县级宣讲员。在五寨县,“宣讲长于三十一日抵县,派六区团长联传村长五十余人齐集城内听讲后,即令回村宣讲”.省级宣讲员冠以“宣讲长”之头衔,而各村村长成为事实上的“宣讲员”。
政府还采取分发文告,即散发传单的方式,向民众普及肺鼠疫流行及预防之知识。1月28日,阎锡山给防疫前线的县知事、县佐和警佐的一份电报,指出迅速将防疫文告张贴至村庄的重要性。另外,“特谕村长副,两单各印二十余万张,遍寄乡村。据委员调查报告,各村庄自行防范之严,得力于印刷物者居多”.如果以每个村庄50人计,20万个村庄包括1000万人口。1918年,山西全省人口大约1200万.如果每个村庄的人口更多一些,20万个村庄几乎包括全省所有的村庄。
这40万份传单是通过以下一些途径下发给村庄百姓的。1月31日,阎锡山致电驻扎在宁武县的马旅长:
井坪疫势蔓延,仰速电朔县,速将本署警告人民须知分送各村,使人人笃信遵行为要。
2月14日,阎锡山通电雁门道属各知事暨岢岚等16县知事:
现因防疫吃紧,业经邮发六言布告,晓谕人民。各知事于收到后,速行分散各村镇,责成村长副及首事人等切实与人民讲解明白,以期由信生畏,各知自防,以补官力之不及,仍将分散地方报查。
通过分级宣讲,通过传单发放,民众动员的目的基本达到。以此为基础,阎锡山可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实施隔离,并全然不顾疫事初起时对于“父病不让子侍,夫病不令妻侍”这种不合中国伦理的隔离措施的种种顾虑。
上述各种事实证明,1918年年初山西防疫的展开,是中央政府与山西阎锡山政府通力合作的结果。以此角度观察,1918年山西的肺鼠疫防治,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
疫后之疫
是鼠疫还是禽流感
虽然在1918年年初发生肺鼠疫流行的28个疫县中,没有兴县和临县,却不能说兴县和临县不是疫区。1919年1月26日,《申报》刊载内务部前一天所接阎锡山拍来的电报,电文云:
内务部鉴,寒电诵悉。自本月九日后,迭据临县知事先后电称,薛家村附近之香草焉高恒成家疫死者四口,水草沟高尔成家男女疫死者九口,薛家村薛仲由家疫死者三口,薛毕广家疫死夫妇二口……嗣后据电称,近来严加防御,据查各村现在染疫者,仅有数人……此外尚无染疫病人发见。约数日内可期肃清。
鉴于篇幅,上文未能全引《申报》全文。在《申报》全文中出现的村名有薛家村、香草焉、水草沟、崇条岭、王家坪、乔家坪等六村。在1962年的调查中,只有王家坪证实于1918年秋天流行过鼠疫。(大)乔家坪鼠疫的流行,发生于1929年。在现代山西地图集中,可以查到香草焉、丛条塄、薛家焉等三个地名,“丛条塄”可能为“崇条岭”之音转,“薛家焉”可能为“薛家村”。据此可以确定这一片村庄的大致范围,位于临县西部离黄河大约10公里处。“乔家坪”应是后文所揭其他报导中的“乔家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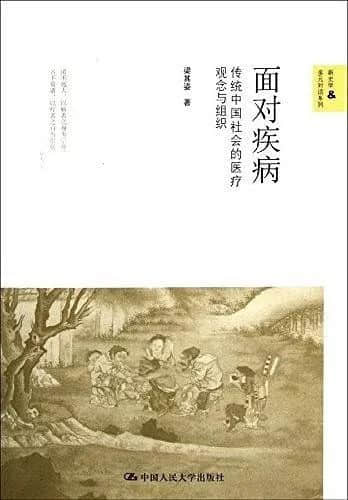
电文接着说:
再者,此次疫症仅限于县属西隅王家坪等七村,其余各处并无传染等语。查该县自疫症发生以来,计已疫死七十人。前派汾阳医士王家全、王兴赴临检验,尚未能确实认为肺疫,已于十六日加派西医万德生前往检查。
时任汾阳(州)医院院长的美国医生万德生(Percy T.Watson)亲赴临县,事后撰写了一份有关防疫工作的报告,详述见闻。[37]万德生报告了王家坪村一个王姓家庭(族)共30个成员的死亡情况,此不赘引。万德生还报告,通过亲戚探病,掩埋死尸,其他村庄的中医前来看病等三条途径,王家坪的疫情传染给其他村庄。并且,所有这些死亡者都被认为具有肺鼠疫的临床特征。具体的症状,上引《申报》同日同版引西文《大陆报》在汾阳的通讯员称:
盖临县知事曾呈报太原,谓距黄河东十五英里山上数村,有传染症,患者辄吐血,已死多人……万德生医士接电后,即派去年偕往治疫之员二三人,前赴疫地。日昨派出员报称,临县疫症患者,吐黄沫与血,察其症状,颇与去年肺炎疫相似。
然而,到达临县后,万德生等对一例死亡患者的肺部病理切片进行显微检查,却未发现鼠疫菌。1918年春天山西肺鼠疫疫区距离临县最近的也有4天的路程,疫情不可能传入。于是,万德生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释。1918年,世界范围内的“西班牙流感”(即禽流感)肆虐,导致20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万德生认为1918年10-11月,西班牙流感曾经掠过这一区域,临县发生的疫情,有可能是西班牙流感。
万德生认为,从临床症状上看,西班牙流感与肺鼠疫极其相似。西班牙流感是致命的,很少有人染疫后能活过三天。许多人在染疫后的两天或更短的时间里死亡。对西班牙流感病亡者的尸检与对蒙古地区肺鼠疫死亡者的尸检有许多相同之处。黄色的咳痰和血浆也与临县疫情中的一些案例相同。医学文献已经报导了西班牙流感和肺鼠疫的病理学发现的相似性。不过,临县的疫情究竟是什么?是肺鼠疫还是流感?万德生医生还是拿不定主意。

在1962年的调查中,调查员已经注意到这次疫情中王家坪、乔家沟、贺家窊、圪旦上四个村庄疫死人口92人。圪旦上和乔家沟均与王家坪为邻。贺家窊不见标识,应是村庄较小的缘故。另外,1919-1920年,王家坪所属雷家碛公社(乡)下辖之张扬沟、西沟和新化三村共疫死人口112人,说明王家坪一带是1918-1920年临县疫情之中心。这一点,与上引1919年临县知事发给阎锡山的电报是一致的。
伍连德1929年报导,1918年秋天临县刘家山发生腺鼠疫患者30人,王家坪及另外九村发生91人,病型不明。1919年,疫情传至兴县白家山,病型仍然不明。[38]1962年,山西省卫生厅组织调查,1918年在临县的刘家山等10村病死181人,兴县刘家峁村有鼠疫流行,死亡8人。关于疫情的性质,山西省卫生厅认为1918年秋天临县的病例证明是腺鼠型;该县青凉寺公社大石级的患者发生在10月份,距本年肺疫在山西的流行时间(1-3月份)相当久,且经过一个夏季。所以,“1918年临县人间鼠疫的开始发生,与本年发源于内蒙西部的肺疫流行没有明显的关系”。
具体地说,在1962年调查的全部疫村中,有症状记载的有52村次,其中全部为“起核子”(即腺肿)或有起核子者为39村次,占75%,疑有“起核子”者7村次,占13.5%.此外有“吐血”者、“吐黄水”者和“点瞌睡”者。“点瞌睡”者的症状不明,究竟哪两村出现“吐血”者和“吐黄水”者,山西省卫生厅的调查员语焉不详。尽管如此,1962年的调查员还是确定1918年的王家坪疫情,是腺鼠疫,不是肺鼠疫,更不是西班牙流感。
1962年所调查的97个疫村次中,有流行时间记载的为42村次。“开始流行时间最早在旧历六月份,流行停止时间最晚在旧历十月份”。王家坪村的疫情开始于1918年12月12日,结束于次年1月25日,最大的可能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的肺鼠疫。万德生称,他们“在临县疫区的14天中,没有找到腺鼠疫之痕迹。鼠中也未发现任何其他疾病”。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如果说旧历十月腺鼠疫流行已经结束,两个月以后如何找到痕迹?1962-1974年,山西的鼠疫防治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然他们相信历史时期临县一带曾经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2004年7月我在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即原省卫生防疫站)访谈,有关专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对于这一疫源地消失的原因,仍不知详。
不过,1962年的调查者显然没有将1918年12月王家坪村发生的疫情纳入调查范围。如果纳入,是疫延续至1919年1月,且按照万德生所称,与王家坪村约有几里路远的“丛条塄”村,也是疫区,至少有十几人死亡。这个村庄未列入调查者所列疫村名单。山西省卫生厅的调查人员可能没有读过《申报》的相关报导,却读过万德生的报告,只是不知为何,他们对于相关内容未予讨论。
西医和中医的实践
1918年春天山西疫情刚刚平息,秋天临县疫情又起,冬天疫情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在的疑问是,作为山西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的阎锡山为何不能再次进行全民动员,扑灭临县疫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即使临县的疫情不是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西班牙流感,政府也有迅速扑灭疫情,保障人民生命之安全之责任。更何况西班牙流感对人民生命之威胁,并不低于肺鼠疫。
根据上引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可知阎氏对于临县的疫情,“仍督饬该县加意严防,以期完全扑灭”。而据同日《申报》引《字林西报》:“内务部接山西消息,据谓临县曾发生疫症,共死七十人。当即隔断交通,染疫者迄今只有七村。自一月十七日起,未有死于疫者。疫势有肃清之望。”疫情没有蔓延。又引《大陆报》:“太原警厅长于一月前印就公函,分致各城村,告以疫症复作之危险,并示以辨别疫症,防其蔓延之方法。此种举动颇有效力,故山村一见疫症之发作,即呈报知事,而知事即据以转报省长焉。”万德生的报告与此不同,他说:“虽然第一例死亡发生于1918年12月12日,但直到1919年1月5日疫情并未上报。”及时上报疫情是1918年山西肺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年冬天,临县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根据1962年的调查,从1918年至1932年,临县几乎年年有鼠疫疫情发生,兴县则延至1939年。在临县,1924年和1931年的疫情最重。1919年秋天和1924年秋天的临县疫情留下了相当详细的报告,值得讨论。
1919年10月3日,临县胡知事向省长阎锡山报告如下:
本月漾日下午三时,据第四区长郝乾昭报告,西区距城八十里之张家沟、山庄头两村,有时症发生。立派警前往视察,据该警等回报,张家沟已死男女三十人,山庄头已死男女二十人,尚有病者十口。据称病初起,头痛渴睡,有发热者,有患寒者,有头肿者,有腋下或胯下生一硬核者,三四日即死,流行甚速。又称西沟村亦有此病。除派警佐带警前往依法防治外,谨先电问。
从上述患者临床症状看,临县发生的疫情为腺鼠疫无疑。据1962年调查,西沟村疫死85人,且不见张家沟和山庄头两村。或村名有变,或张家沟和山庄头属于西沟一部分。与前述王家坪村属同一区域。同一资料记载,“兼省长接电后,甚为忧虑,立即饬知中医改进会照该知事呈报情形,妥拟治疗方法”。中医改进研究会立即判断是疫为“疙瘩瘟”,头肿者为“大头瘟”,并订出相应药方。同一消息及药方于二日后在《山西日报·星期附刊》上再度刊登,从此不见下文。
万德生也再次进入疫区。10月17日,在疫区兔坂村工作的万德生报告当地9个村庄共有220人死于腺鼠疫。至他撰稿时为止,每日大约有3人死亡。如果不得到控制,随着冬天的来临,腺鼠疫有转为肺鼠疫的危险。[43]至此时,他已经确定临县的疫情为鼠疫。
另外一份文献详细记载了1924年几名中医和西医前往临县防治疫情的经过。是年10月新家茆等村发生疫症,死亡500余人。中医改进研究会“以疫势如此险恶,蔓延如此迅速,一面按照急性险疫疗方,具覆省署转示该县,一面选派中医薛复初、赵儒珍、西医安增寿,即日携带药物前往该县,尽心疗治,筹划预防善后各方法。”在1918年参与防疫的西医名单中,有医生名安寿增,省籍为直隶,疑与1924年派往临县之安增寿为同一人。《医学杂志》同期还刊登赵儒珍所撰《临县防疫记》,赵氏称:“本年阴历九月九日医士等奉省长委派,往该县防疫,比至该县,业已死亡五百余名。”与1919年的情况相同,阎锡山相信中医具有防治腺鼠疫的能力。
1924年鼠疫血清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根据赴临县医生之报告,鼠疫血清是向汾阳外国医院借得的,共110余瓶。三位医生从临县县城赶往疫区之前,均注射了鼠疫血清,以至于路上“药性发作,头痛发热”。1918年肺鼠疫流行时山阴县某中医死于非命。1919年,万德生报告也提及有中医死亡。 1924年的情况大不相同,防疫医生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
山西中医对于鼠疫的观点也有了变化。例如,赵儒珍所撰《临县防疫记》就接受了西医有关鼠疫病因的解释。他说:“其传染情形为由最接近病人者,以渐扩充,受传染后,多数淋巴腺肿胀化脓,鉴别诊断,知为腺肿鼠疫(l )riisenpest),而媒介体则为蚤虱蚊蝇之类。”中医赵儒珍会用西文标识病名,也知道腺鼠疫通过蚤类传播,显然是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成果。不过,将虱及蚊蝇之类也当作腺鼠疫之传播媒介,则是他的想当然。
与赵儒珍的观点不同,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报告完全站在中医的立场解释鼠疫。《防治临县疫症记》称:鼠疫流行的起因主要是“今岁春夏亢旱,热度过高,热毒内伏,秋深始发,此关乎天时者也。该县四区,前岁曾发生鼠疫,其根潜伏未尽,铲除此关乎地气者也”。早在1894年,医学界已经证明,导致鼠疫流行的是鼠疫杆菌。此次赴临防治鼠疫的医生从岔沟村一名苏姓病人体内也检出鼠疫杆菌,与“气”无关。
根据以上两份报告,在临县鼠疫防治制度方面,可以知道以下事实并提出相关疑问:
其一,在省派医士未到达之前,临县知事指挥警佐,对疫区实行隔离。不过,10月16日抵达临县的医生向学会报告时,临县全县疫区多达27村,死亡人口多达500余人。仅从此数,亦可知在省城医生抵达临县之前,该县不存在有组织的、规模性的、有效率的防疫。
其二,赵儒珍医生称:“病源虽已明了,而处治之方殊无把握,惟有注意隔离及消毒、清洁等法。”民贫而浊,清洁之法实难办到。消毒之法,主要包括熏屋和处理大小便和唾物。隔离之法的难点不在于隔离,而在于隔离以后如何处置,即如何保证食物和衣被的供应。赴临医生重申1918年阎锡山所定之隔离原则:“宁牺牲一人,不能牺牲一家,宁牺牲一家,不能牺牲一村。”按照赵中医的说法,在他们赴临十余天后,由于采取的隔离措施有效,“疫势渐就扑灭”。不过,如上文所揭,1924年临县疫死人口多达959人,有400余人是在省城医生抵临后死亡的。疫情似乎没有得到如此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另一种可能则是,在省城医生赴临之前,临县疫死人口已经不止500余人,而是更多。
其三,关于治疗方法,11月2日,赴临医生写给研究会理事长的一份信中有如下陈述:
前函报告新发生疫症之薛家峁及疫症复萌之三两村庄,共有病人八名,职等筹思预防方法及治疗方法,除隔离外,惟有施行血清注射。其法于现病者每人注射一瓶,三日后观其效力若何,病若不退,再续行注射。预防者每人注射半瓶或一瓶三分之一,先注射现病者,次注射疫死病人之家属,最后注射现有疫症之村人。
现无资料揭示1924年的抗鼠疫血清对于腺鼠疫病人的治愈率。医生只是报告说:“所幸刻下疫症范围极小,注射而外,加以严厉隔离,或可消灭净尽矣。”赵儒珍在其报告之最后指出另一种疗法:“于此经过之中,获一较好疗法,即刺破化脓之腺肿,内服清解之药剂,藉以活人不少。此可以供医学界之研究者也。”完全未提及抗病毒血清之治疗方法及功效。
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所撰报告中,有关于治疗鼠疫的详细中药配方,所用无非中医清热解毒之药物,如连翘、黄芩、桔梗、陈皮、银花、柴胡、甘草、生石膏、滑石之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这类在中医看来能够“清火泻毒”的药物,不能证明可以杀灭人体内的鼠疫杆菌。另外,在“西医治法”和“中医治法”中,都有关于划开疙瘩,病者立愈的陈述。这一治疗方法得不到现代医学的证明,存疑。
1929年9月27日,《山西日报》第6版有关于兴县罗峪口及临县第四区的疫情报导,并涉及稷山县。不过,稷山县患者临床症状只是“腹痛头晕,直吐不止,二三日即死”,疑为霍乱。有关罗峪口的报导,因文字漫漶,无法识读,但残缺文中留有“血”和“疙瘩”二词,可以断定为腺鼠疫。1962年的调查也证明这一点。临县疫村为修化村,在1962年的调查中,写作新化村。这些报导之后,并未见后续报导。只是在临县“幸未蔓延他处,现已完全扑灭”;在兴县,“情形甚属可畏,该县县政府,虽力事预防,而迄无少减云”。鼠疫防治,完全成为两县的地方病防治。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1918年以后,阎锡山政府对于境内鼠疫防治的关注,日减一日:从1918年的全民防疫,演变至1919年和1924年的有限关注,至1929年,几乎完全成为县级政府的地方事务。本文的问题是,同样是山西鼠疫的流行,何以在1918年秋天以后,不再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却转化成为“地方的公共卫生”?
传染病:从国家到地方
临县和兴县位于山西省之西部,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榆林地区相望。两县境内海拔多在1200米以上,东部的吕梁山海拔较高,不少山峰海拔高度达到1600-1800米,造成东西方向的交通阻隔。时人称临县“距省五百余里,万山丛杂,交通极感困难”。在上引文献中,万德生有关于当地交通的如下说明:
尽管临县位于太原府西北部不远,但这个区域相当封闭,必须通过太原府西南的汾阳府转至临县,从汾阳府至临县的80英里道路最好。从一年前发生肺鼠疫山西北部最近的疫区到达临县,大约要化四天的时间。该县无商路与外县相通,与外部世界几乎无甚交流,也不需要购买燃料或其他生活日用品。
尽管从汾阳城至临县的道路最好,但是,万德生一行一路走来,还是化了五天。从地理的观点看,临、兴两县地表多为黄土覆盖。因长期受到流水侵蚀,地貌破碎,部分地区形成梁、峁状地形,县内交通极其不便。根据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的提示,笔者注意到临县和兴县的疫村均分布于两县之西部。如在临县,民国时期所有的鼠疫疫村,均分布在湫水河以西,河东绝无疫村的存在。细究之,在临县,黄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县内各大小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河流切割造成地形的阻隔,县内东西交通极为不便。兴县的情况与临县相似。准确地说,两县鼠疫只是两县西部地区的地方病,从未传播至两县东部地区。
对于山西省政府而言,既然临县、兴县的腺鼠疫只是两县的地方病,所以,也就不用进行全民动员,进行大规模的防疫。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然临县、兴县的疫情对山西其他地区都未造成威胁,管他何干。1918年山西肺鼠疫之防疫与疫后之腺鼠疫之防治之所以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关键就在于传染范围的不同。1918年从内蒙传入的肺鼠疫,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波及山西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灾难,而临县、兴县之腺鼠疫,本质上只是这两县的地方性传染病,与山西其他县域无涉。
吕梁山造成临县、兴县与山西东部各县交通的阻隔,但由北自南流径兴县、临县的黄河,却为两县与外界的交通,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临县,湫水河流入黄河的碛口镇,也因此而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1918年防疫中的两道防线均以此为终点,即可证明这一渡口的重要性。1928年,流行于临、兴两县的鼠疫渡过黄河,西传至陕西,最终在陕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据陕西省卫生防疫站1966年调查,1931年横山、米脂、子洲、葭(佳)县、绥德、定边、吴旗、子长、清涧、靖边、榆林、安塞、吴堡等13县流行鼠疫,共死亡9648人。疫情相当严重。鼠疫疫型主要是腺鼠疫,到秋天,有转为肺鼠疫的倾向。
1931年参加山陕防疫工作的陆滌寰医生引用一份地方防疫会提交的各县疫死人数报告,取整数为7440人,如果考虑到1000余人,100余人的“余”数,疫死人口与1966年的调查相近。不知何故,陆滌寰不相信这份报告。他不仅认为疫死人口远远多于报告人数,且相当主观地估计疫死人口在2万以上。除此之外,有调查者称,“由西安所得之情报,谓死亡达五十万人之多”。但据叶墨(Jettmar )和万德生的估计“其死亡者约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这一以后证明为错误的数据,影响巨大。南京国民政府下令:
现查山西、陕西两省地方发生鼠疫,人民罹其灾者,死亡甚多。若任蔓延,贻害胡底。亟应设法防范,迅图救济。著行政院转饬内务部,遴选卫生署医官,带同助手、护士及各项药品,迅即前往,会同各该省政府,妥速办理,以期疹疬潜消,民生咸遂,是为切要。
1931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临县碛口镇设立山陕防疫事务总处,分医务、总务、秘书、调查四股,以万德生任主任,并派有西医若干,指导山陕防疫。陆滌寰医生于11月12日抵达疫区。
据陆滌寰报告,20余名防疫医生由各地派遣而来,地方政府亦派有医生,从事防疫和联络工作。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防疫机关外,山西省设有省防疫处,由省民政厅长兼任防疫处长,省立医院正副院长担任正副主任,指挥全省的防疫工作。鼠疫流行的各县及其邻县设有防疫局,县长兼任局长,并由具有防疫经验的医师任副局长,下辖若干名防疫医生和调查员,从事本地的防疫和调查工作。除了防疫处和防疫局外,省里组织有防疫委员会,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充当委员,也为防疫处提供咨询。与山西省类似,陕西省各县也设立防疫局,由省政府派遣医生若干名。并在榆林县设立陕西临时防疫处,从事陕西鼠疫流行各县的防疫工作。很显然,与1918年初的情形相同,1931年的山陕防疫显然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
由于资料缺乏,关于此次防疫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抗鼠疫血清被普遍应用的1924-1931年,对于鼠疫的防治应该较以前更有效率。只不过,山西省政府已经失去1918年的防疫热情,1918年的全民防疫不复重现。
或有人言,1924年秋天,正值阎锡山介入直奉战争,无暇他顾;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处于隐居状态。两次战争有可能是导致阎锡山无力防疫的重要原因。笔者之所以不同意这一观点,是因为从1918年至1939年,临县、兴县的鼠疫疫情就没有停歇。据上引资料所引1962年的调查,临县1927年疫死760人,1928年315人,1930年318人,1932年650人。兴县1926年疫死215人,1928年289人,1929年532人,1932年518人。就每县疫死人口而言,大都超过1918年初的水平。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省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不作为,反映的是防疫观念的改变。
根据流行病学的分类,鼠疫属于与天花、霍乱并列和三大烈性传染病,其疫情的发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视作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与传统时代相比,近代政府具有更为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军事、行政以及其他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疫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从来就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扩散且构成对于其他地区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那么,此类疫情所涉仅仅是“地方的公共卫生”。虽然国家由一个个地方所构成,但单一的地方本身不等于国家。除非当地方性的危机突破地理的篱藩,形成为跨地方的危机,或直接形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地方的公共卫生”才有可能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转化为“国家的公共卫生”。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临县和兴县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流行,因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长期被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以一种类似“地方病”的方式存在,并不构成对于邻县人民生命安全之威胁。因此,两县鼠疫及其流行,长时间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之范围。在本案中,临县境内的黄河和湫水河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扩大点说,则是黄河和吕梁山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上引《申报》载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复据沿河营县报称,专员赴陕调查,亦无肺病传染,似不至蔓延为患。”是将黄河作为边界。《申报》引英文《大陆报》之相关报导后,又称:“按疫区距汾州、太谷、太原所在之平原,相去仅三日路程,故此间教会已行预防方法,军警亦设法防疫。”已经感到吕梁山西侧的疫情对于东侧平原的威胁。可见,1918年秋天以后,“地方与国家”在黄河与吕梁山脉划定了彼此的界线。1931年,山陕防疫事务总处设于临县碛口——一个黄河边上的重要渡口——就是此前地方与国家的象征性分界。
再将话题展开,以山西省的情况看,“民众的个人卫生”是一个更加令人头痛的话题。赵儒珍医生称临县人民,“民贫而浊,惯性不易改除”。具体的描述如下: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 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制,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陆滌寰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将临县一带居民的掘窑洞而居称为“穴居”。在他看来,窑洞中的不卫生,以及谷物和其他食品在窑洞内的储藏,极易吸引鼠的进入,引起人鼠接触,导致人间鼠疫的发生。
1931年,山西省各级公安局开展卫生调查,其调查项目是街道市场是否清洁、河沟水井是否清洁、(不具资格的)医师医院如何取缔、茶楼酒馆如何检查、妓院戏场理发所如何管理、卫生教育是否创办、防疫事项有无设施、适合卫生之工程有无计划等共八项。这一工作不知是否与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山陕防疫有关?
依据同书记载,事件性的瘟疫流行与防治暂不讨论,就常规情形而言,在山西各县,日常的公共卫生只限于打扫街道,建设厕所。日常的卫生防疫设备大多只备有石灰而已。如在吉县“查职局仅备石灰一小尾,以备使用之外再无设施”。所谓“职局”绝不是卫生局或防疫局,可能是公安局。
另一资料简单地记载山西防疫机构是疫来则设,疫停则撤。如太原,该县于民国二十一年秋季“因发生虎疫曾疫立防疫局一处,后以疫势扑灭经停办”。如新绛,同年秋间“因发生虎疫,临时召集士绅、医士组织防疫局,现已撤销”。所谓“虎疫”,是霍乱之译称。以临时性的机构来组织对于预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工作,实际上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仔细研究这两段资料还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城市或市镇的。在1930年代的山西,政府尚无力在农村推动卫生运动。1918年初,阎锡山政府曾经制定通过公众场所、家室与个人的清洁、消毒来抑制疫病的“清洁及消毒法”,只具应急的性质。也就是说,近代政府可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甚至暂时建立某种制度,但却无法改变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状况,无法改变“民贫而浊”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按照现代公共卫生理论,拥挤的居住空间,光照不良,通风不畅,住房兼做贮藏,人与动物共居一室,都在为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创造着条件。“民贫而浊”使得“民众的个人卫生”不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的公共卫生”只不过是个人卫生的常态展现,“国家的公共卫生”则是个人卫生的危机展现。民众生活的不卫生,既挑战“地方的公共卫生”,也挑战“国家的公共卫生”。由于“民贫而浊”是人民的生活常态,不可能构成公共卫生的“事件史”,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重大疫情的经常性爆发与国家动员机制下的“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就成为那个时代公共卫生的显著特征。
政府与公共卫生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有组织的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既然是“有组织的”活动,也就是政府的活动。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在传统时代,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具体地说,政府的工作与预防疾病、延长人民寿命和促进人民健康无关。1910年,满洲里肺鼠疫爆发流行,清政府指派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伍连德博士赴东北防疫。伍连德通过调动军队、停运火车、严格防疫等一系列手段,迅速扑灭疫情。1911年4月,清政府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即今天所谓“鼠疫防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中有来自英、美、俄、日、德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共35位。伍连德任大会主席,并被后人誉为“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考虑,1910年的东北防疫,可以视作中国政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17年绥远疫起,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防疫委员会,在各省成立防疫专门机关,制定卫生法规,划定区域防疫,以及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等[63],都可以证明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烈性传染病流行带来“公共卫生灾难”构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正如1918年阎锡山所理解的,卫生防疫也就成了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卫生防疫,便成为近代国家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时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卫生内容逐渐增加。从1940年代开始,政府介入地方病防治,1950年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和全民健康构成公共卫生的主要内容。将这一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历史演变,不难理解1918年的山西防疫及疫后之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地位。
1918年的山西防疫,是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合作开展的对于烈性传染病的全面防御。1918年秋天以后的山西疫情,是烈性传染病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地方病——一种与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相类似的地方病。人们对于疫情的关心,有时并不是对于疫情本身的关心,而是对于疫情流行边界的关心。这样,某些特定的河流与山脉便成为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责任的边界所在,也就成为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所在。这样一来,公共卫生也就演变为“地方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的公共卫生”。直到1928年以后,疫情越过黄河,并于1931年在陕北酿成大灾,中央政府才强行介入。由此可见,1918-1931年的山西鼠疫防治过程,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转化的过程。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内蒙、东北乃至满洲里以北的俄罗斯境内,到处聚集着来自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的人流。他们从事农业垦殖、捕猎、砍伐、开矿、贸易和其他生产或经营活动。1910年和1918年,东北疫情和山西疫情起时,都在农历岁末。按照传统习俗返乡的人潮汹涌,铁路交通使得人口的流动更加快捷,疫情传播更快。面临危机,两个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作出了迅速且有力的反应。临县、兴县的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居住于山区的当地居地甚少与外界交往,疫情传播缓慢。与此相应,中央政府仅表达了有限的关注,而地方政府的反应也相当迟缓,处置不力。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同一疫情,政府采取不同的因应之策,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交通条件的改进,流动人口更多,流动速度更快,“地方的公共卫生”不再存在,传染病——尤其是烈性传染病——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公共卫生”。
本文最后还想指出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直至民众完全溶入国家体制的过程。只不过,这一点将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主题。
转载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作者:曹树基,来源: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