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6日是惊蛰,雷声响起,广东进入了前汛期。在锋面和低空急流的作用下,带来了连场暴雨。灰黯的、乌紫的浓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瞬间聚拢成海,朝同一个方向疾驰。风雨交加,雷声沉闷而持续,好像地壳深处有什么东西睡醒了;大雨如同一幅不透明的白色布帘从天而降,被风吹得上下翻滚;迅猛有力的雨点,落在朦胧的珠江水面、落在大街小巷,噼啪作响,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被风收走。
这场暴雨,似乎要把大地郁积了十几年的闷气、怒气、怨气、烦气、病气,一次过痛快地倾吐出来,荡涤净尽。
每个人都感觉到,舞台正在搭起,鼓点愈敲愈急,灯光由暗转明,帷幕一点点拉开,一出气势磅礴的历史大戏,即将开演。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第二天,该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这是序曲的奏响。过去与未来,都将在这场暴雨中,飞扬、起舞、喷发、沸腾。中国人的面前,再次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多少人在风雨中等待,倾听雷声,期待明天会虹消雨霁,阳光灿烂。
所有人都在等着明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都在等着。

1978年是不断上演奇迹的年份,难以置信的消息纷至沓来,让人相信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奇迹。这一年,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被撤销;中小学的农村分校一律停办,升学考试也恢复了,昨天还土头灰脸的老师们,今天满面春风回到了课室里;右派一律摘帽;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了;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统统除去恶名,可以正常做人了;堆积成山的“文革”冤假错案,开始复查,几年前,一群广州青年张贴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轰动全国,被诬为反革命集团,也悄悄平反了;当年的“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被扫地出门的“臭老九”们,红光满面地回到原单位,教书的继续教书,演戏的继续演戏,作画的继续作画,写诗的继续写诗。广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举办“新年诗歌朗诵会”和“新年音乐会”,广东画院举办习作展,文化公园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广州动物园来了一批新动物,有四不象和黑猩猩;市花木公司养了30万尾金鱼,准备在春节游进千家万户;流花湖公园新开辟的芙蓉洲游览活动区开放迎客了;荔湾湖公园建了一座可以搭载52人的电动转盘,上面有小马、小鹿、飞机、飞船,小朋友的尖叫声与欢笑声,在湖面回荡,让人感觉到处处是春天的骚动。
当《人民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年轻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时,社会沸腾了,多数人对文中引用的公式、定理,都是云里雾里,作者本人大概也不懂,但因为以科学家为主角,足以造成巨大轰动:时代要变了!科学重回舞台中心了!作家们也万分惊喜:原来不是非要写工农兵不可了!
消失已久的“珠江夜游”再度起航;端午赛龙舟的鼓声咚咚擂响;各种体育协会恢复了;第一批特级厨师、点心师、糕点师、宴会设计师、肉食加工工艺师、钟表修理技师、配镜验光技师、理发师、摄影师,喜气洋洋地领到了证书。《广州日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泮溪酒家特级点心师罗坤、北园酒家特级厨师黎和、特级点心师陈勋、肉食加工工艺师廖干、宴会设计师徐少荣和南园酒家特级厨师刘邦。据说罗坤会做一千多款不同的点心,有九位日本人不相信,跑到泮溪酒家,要求他每天做16款不同的点心,4款甜的,12款咸的,价钱还要不低于16元,连做一个月。罗坤欣然接受。这几个日本人吃了一个星期112款不同的点心后,彻底折服了,自动放弃继续试吃。罗坤名声大噪,应邀到服务行业的“七·二一”大学讲课,传授点心技术,编写《广东点心》专著。这真是一个扬眉吐气的高光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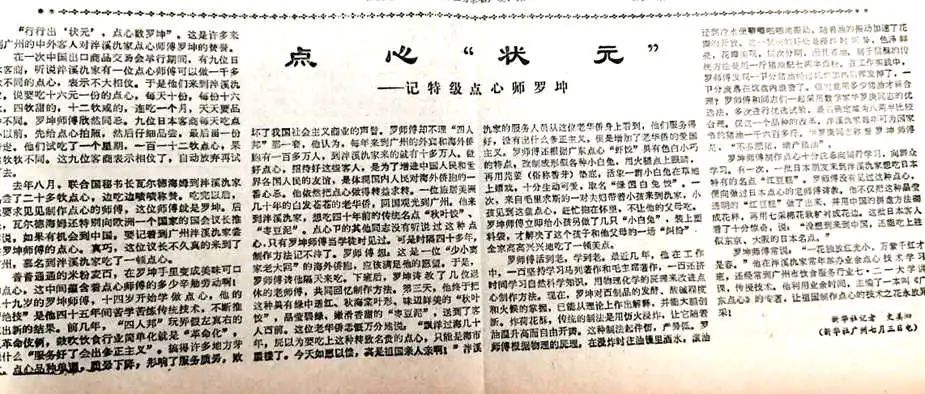
尽管特级厨师、特级点心师、宴会设计师的手艺,博得世人赞叹,但在平头百姓看来,那些都是为外宾服务的,广州人的梦想其实很简单,不是每天吃16款不同的点心,而是不用再为“七鲜”(鲜菜、鲜肉、鲜鱼、鲜蛋、鲜奶、鲜果、鲜花)发愁。广州历来是“近郊种菜,远郊种禾”,1978年的广州市民,每天要吃掉230万斤蔬菜(一年到头只有19天吃菜少于170万斤),全靠扬箕、猎德、岑村、冼村、石牌、三元里、下塘、望岗这些近郊农民提供。但在“一大二公”体制下,农民连种菜的兴趣,也几近消失殆尽,菜市场经常空空如也。
农村不改革不行了。改革就从蔬菜开始。广州市农业委员会的蔬菜处,进行了一项改革:让蔬菜的价格,适当灵活一点,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波动,上限为40%,下限为20%。1978年7月21日,他们拟了一个方案,尝试放开蔬菜价格,用价格刺激生产。广州的蔬菜价格一下子涨了40%,白菜一斤涨了两分钱,引起了轩然大波。工厂有些工人气愤地摔碗摔碟,大骂菜贵。甚至部队也有反应。
当晚,省、市革委会相关人士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紧急刹车,第二天又召集郊区的公社书记、市区的区委书记,到越秀宾馆开会,下令中止这项改革。好在从第三天起,菜价开始回落,成效初显,给了“放开派”一些事实支撑,但因为“上头”已大发雷霆,不得不暂时止步,重新调整。最后“放开”与“收紧”的意见达到妥协,把价格浮动的幅度,调整为上限20%,不设下限。

价格浮动,固然是一记妙招,生产队收入增加了,但怎么让钱进农民口袋,才是成败关键。1978年广东农村的人均收入,只有区区77.4元。广州东郊有一条扬箕村,开村于北宋年间,历史悠久。1951年扬箕村成立姚浩鹏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华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四个互助组之一。1958年扬箕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称生产大队)作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派代表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但花团锦簇的外表,难掩一穷二白的现实。1978年,这条有四千多人的古老村子,集体存款只有150元,固定资产59万元。
办法就是搞包产到户。扬箕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田分给农民自己耕作,种下了芥兰、冬瓜、椰菜、菜心和白菜等蔬菜,运到东山、龟岗、黄花等市场出售,月收入一下子从不到10元猛增至30元,很快又长到100多元,大家喜笑颜开。整个郊区都跟着搞起来了。什么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据当时的解释是:“这个‘包’字实际上分两个阶段,刚开始叫联产责任制,后来才是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是不同的。初期阶段就是分给你一亩菜田,定一个写成额,超产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比如规定一亩要收5000斤菜,要是你收到7000斤,那多出的2000斤中的80%归你,20%归生产队,这叫联产。”
尽管没有大肆宣扬,但承包风在全省农村迅速刮起来。从化江浦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三个生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炭步公社大涡大队,也试行“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人人都喜欢“包产到户”的,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味道”太浓。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农村部一位副部长严厉责问广州郊区的领导:“你们郊区胆子大了,你搞包产到户,考虑后果没有?”
这位领导说:“这是联产责任制嘛,不是包产。即使是包产也没有错。”
“你知不知道后果啊?”
“有啥后果?最多不当这个郊委书记。”
不搞联产承包,农民没有活路,这就是结论。1979年9月,广州市有五十多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六十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像神话故事一样,凡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集体与个人收入,都出现节节攀升。下一步,包产到户,水到渠成。农民们在大队的宣传栏,贴上“包字万岁”的口号,他们的坚定信念就是:“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永远不能富。”一年以后,广州市已经五十多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六十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
这时又有另一股潮流,悄悄涌起。1978年的春季广交会上,一位南海籍的香港商人,想委托大沥塑料厂,生产一种国外流行的塑料袋,也让自己家乡发点小财,但这家厂设备简陋,既无技术,也无原料,生产不出来,令港商大挠头皮。这时,广东的外贸人员劝这位港商,不如赠送一套设备和三千吨原料给塑料厂,厂方收取一些加工费,并逐步从产品出厂价格中扣除机器和原料成本。生产每个塑料袋1元钱,塑料厂收取0.15元的加工费。这位港商一计算,觉得“有数为”(划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种模式被广泛复制,顺德大进制衣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南海大沥塑料厂,几乎同时诞生,成为第一代“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

这才不过是个开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多想,只知道办工厂好过下田,挣钱多,不用两脚牛屎、日晒雨淋。东莞办的那个太平手袋厂,工人工资比县干部还高,很多人拎着鸡鸭走后门,都想挤进厂里工作。广州郊区的农民听到这些消息,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没过多久,大约五年以后,扬箕村的七个生产队,就有几百户农民,洗脚上田,到水荫路的钢瓶五金厂、太和岗的支架厂、服装厂、汽车公司打工去了。他们的田地,被东华实业公司征去开发五羊新邨了。
(图片来自网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