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广东省委宣传部通过南方日报评选“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人物”,一个叫容志仁的广州人,和任仲夷、袁庚、马化腾、钟南山等一起被列为候选人。
跟这些大人物比起来,容志仁并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他早先是个知青,1979年回到广州后无事可干,从街道文化站借了口大锅,投了100元的本钱,在西华路搭了个棚,卖起了早餐。凭借独创的“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的全城最抵早餐,生意越做越好。好到作为广州个体青年的代表,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见,并被书记点名让本地所有媒体报道。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容志仁被胡耀邦、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
按照现在的眼光,当年被“有目的”地包装出的“青年偶像”容志仁,不过是一个摆摊揾食的“走鬼”,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激励了一代人:好多在改革开放后从乡下回到城市的知青,工作没有着落,纷纷在马路边上摆起了地摊。
那真是地摊经济的黄金时代: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政府不但不打压,只要肯做,甚至还把你“扶上马,送一程”。
但之后的“走鬼”,再不曾有过容志仁般的荣光,不会有那样的黄金时代了。
01
1984年,一部名为《雅马哈鱼档》的电影,记录下了当时的广州街头景象——
通街都是地摊,摩托车走得比人还慢。
电影全部实景拍摄。从一个角度看代表着个体经济“生猛”发展的地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造成城市拥堵杂乱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已经六年了,外宾和投资者来广州的次数越来越多,顾及形象的广州,对“街边仔”(改革开放之初对个体户的称呼)也一改之前的放任自流,开始采用“抚剿并用,恩威兼施”的策略。
1984年国庆后,广州明令禁止在带“路”字的地方两旁摆地摊,只有官方划定的固定场地除外。还正式成立了“城管监察队”,主要任务,就是“取缔无牌摊档,对占道乱摆卖的地摊进行清理”。
说白了,就是要把“流寇”,变成“正规军”。你要不愿意被收编,就别怪我不客气。
其中一个允许摆地摊的地方,叫西湖路——一个入驻要交管理费,要办牌照,且只有晚上才能营业的“灯光夜市”。
西湖路灯光夜市地处当时广州腹地,地段极好。但很多“街边仔”不愿意搬进去。为何?一位《南风窗》记者当时问一个“街边仔”,结果被“街边仔”反问:“神经病!你知不知道租一个摊位要多少钱?”
刚开的西湖路灯光夜市,一个摊位电费加管理费每个月要36元——那是个2毛钱就能吃肠粉的年代,这个数字,赶得上当时一些国企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西湖路灯光夜市
虽然铺租贵,但什么都敌不过地段好。
一些希望摘掉“街边仔”帽子的商贩毅然决然租去了西湖路。第一年接近400家入驻,第二年上千家,西湖路的铺位全部租满。
卖衣服的、百货的、夜宵的都来了。西湖路“灯光夜市”,很快就成了广州闻名遐迩的购物天堂、拍拖圣地。
那些没搬进去的倒也没什么后悔的。市区不让在带“路”字的地方摆,那就把地摊挪到桥上,摆到不带“路”字的街道里。和城管打起了“游击战”。
而城管总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现。人群中传来一声叫喊“走鬼啊”,上一秒还热火朝天的路边市集,一阵慌乱,下一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精彩画面”,在1984年之后的广州街头随处可见。
02
也许是场景过于喜感,“走鬼”代替“街边仔”,成了广州人对流动摊贩的新称呼。
称呼的变化,也反映出了广州人对流动摊贩态度的变化,毕竟,“鬼”不是什么好字眼。
城管监察队成立的第2年,市内一家大报刊出通讯员文章:“某些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严重”。
“某些”二字显得含蓄,但明显指向“走鬼”。
在宝华路卖水果的邓伯当时很愤怒。一名走鬼天天在他档口抢生意,城管一来就走,城管一走又来。眼睁睁看着客人都被抢走的他,拍苍蝇拍到水果都烂。
邓伯的愤怒,也是很多拿正牌做生意的个体户的愤怒。他们把生意的不好迁怒于走鬼的非法经营、恶性竞争。加上屡见报端的扰民、卫生、治安等问题,走鬼很快就成了满街跑的大老鼠——人人喊打。
罗文有首歌叫《走得快好世界》,用来形容走鬼很合适——跑慢了不仅要被城管没收做生意的家当,还要被罚钱,甚至被拘留。
一人被抓,整个家庭的温饱都可能要出问题。毕竟做走鬼的大多是些无业游民、或低收入户。抓人、罚钱、收家当,无异于断人生路。
所以冲突时常发生。
1989年秋天的那一次执法,让城管监察队的赖满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与队长处罚走鬼,有人起哄:“打死他们!”队长当场倒地,眼镜都被打飞。
2个月后,一个城管在中山五路罚了一个走鬼10块钱,结果被用剪刀捅伤,躺进了中山医学院的急救病房。
饶是如此,也阻挡不了人们做“走鬼”的热情。
正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90年代,从全国各地涌进来的打工者,大部分进了工厂,进不了工厂的一部分变成了小偷、抢劫犯,还有点道德底线的就成了走鬼。
甚至连本地人,也愿意为多挣点钱把“走鬼”当成副业。1995年的《南风窗》记载:“广州约有40%以上的正式职工从事第二职业”——“这些兼职多是下班后上街摆摊,这才造就了满街的走鬼。”

1997年,刘欢一首写给下岗工人的《从头再来》响彻大江南北: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国企改革“下岗潮”来了,大批下岗工人南下广州谋生。从头再来嘛,做“走鬼”是门槛最低的方式,于是,广州街头的“走鬼”大军更加壮大了。
同时壮大的还有城管队伍。
街头更加热闹了。
整个90年代,“走鬼”是广州街头排在“飞车党”之后的第二大特色。
城管永远在清理走鬼,但等城管一离开,街头又马上变成“走鬼”的天下。
那情形像极了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Tom和Jerry。
03
和动画片中不一样,现实里,胳膊永远拗不过大腿。
2001年,中国加入WTO。朱老总发话:“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偷税、骗税、骗汇、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没过多久,广州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大力整顿,林树森市长亲自挂帅。以卖假货闻名的西湖路等“灯光夜市”被先后关停。
失去西湖路根据地的“街边仔”,有的租了铺,有的转了行,有的汇入了“走鬼”的大军,卖些分不清真假的便宜货混口饭吃。
媒体似乎总偏向站在弱势一方。走鬼猖獗的八九十年代,相关报道大多同情城管。风水轮流转。新千年后,流离失所的走鬼,又成了官方喉舌的关怀对象。
2003年,信息时报策划系列报道《关注走鬼现象》,一改以往批判的笔锋,转而对走鬼充满同情。其中总结了广州走鬼三大特点:外地人、低收入、难觅工作。人大代表纷纷呼吁关注走鬼生存状况。
虽然当时羊城晚报说“走鬼非鬼,城管非钟馗。”但走鬼和城管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2004年7月20日,在员村摆地摊的湖北人李月明被制服男子打死,成了震撼全国的“7.20”事件。——20天前,广州刚刚申亚成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顾耀铭向全世界人民发出邀请:“欢迎到广州走一走。”
确实有很多人想到广州走一走。
一些走鬼老乡自发在员村集合,打算向政府部门抗议城管暴力执法:“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由来已久。”但据新京报报道,此次抗议最终并未发生。
走鬼们真正与政府部门对上话,已经是1128天之后的事情了。
2006年12月20日,新快报发起的一场座谈会引起全城聚焦。水火不相容的城管跟走鬼,破天荒地被请到了圆桌之上,就“走鬼问题是疏是堵”各抒己见。
走鬼代表曾秋花未语泪先流:“我们没有文化,就是混饭吃。”城管支队长王国如立场坚定:“无证摊档绝对不允许存在!”语重心长地提了一句:“要创文明城市。”
文明城市,3年评一次,自2005年实行评选以来,还没见过哪个城市的领导人说过自己不想要的。一天没评上,基层的公务员们就如坐针毡。
2005年度第一届的全国文明城市广州就没评上,当时的市委书记就鼓励大家克服困难,08再战,城管队长王国如不敢懈怠。结果08年广州再次落选,据说公共秩序一项扣了很多分,生态环境未达标,群众满意度低。
创文没创成,市委书记都出来道歉了。市创建办主任很惭愧:“不得不承认,广州在创文过程中是‘打突击’打出来的。”重点打击对象,自然就是曾秋花这样的走鬼。
除了创文,创卫也是广州新千年后第一个10年里的重要命题,前要申亚运,后要迎亚运的广州,门面功夫必须做好。
创文创卫期间,走鬼被列为广州街头“六乱”之首,严打严抓。城管与走鬼之间摩擦不断。谁在暴力执法,谁在暴力抗法?没人说得清,只留下一些血淋淋的新闻事件。
2007年,一名走鬼推着200多块钱水果,刚出街就被城管逮住。半个月生活没了着落的他,一刀劈在了城管肩上,被判了半年。“我不过想讨口饭吃,却陷入牢狱之灾。”
同年7月,黄埔大道员村山顶路段,一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被城管“抓现形”,拉扯之中,妇女的儿子冲上前就给了城管队员一剪刀,直穿腹部。
羊城晚报评论:“几乎每天都有城管受伤。”
走鬼问题,也成了2008年广州公务员考试教辅书里的“十大申论热点”。

04
争议还未平息,又是一场金融危机,珠三角企业倒闭潮,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四川政协委员张平率先建议:“解决就业问题不妨解放地摊经济。”
经济学家厉以宁2009年到广州调研的时候也这样给广州提建议:“小贩也需要就业,不要把他们逼得太紧。多雇人打扫卫生和引导交通就行了。”
一个叫许决华的人不开心了。他是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做过广州城管支队长。他炮轰厉以宁“站着说话不腰疼,读书读太多”。
“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他们限制,反而给他们提供1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明天将会有10万个走鬼跑过来!”——“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此番长篇大论后来被人民网收录进了2009年度官员雷人语录大盘点,即将要办亚运的广州也引来了全国人民的审视。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广州街头有流动商贩近30万,7成属于外地人。大家都想知道,这座以包容著称的城市,要怎么解决走鬼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民生问题。
张广宁市长发话了:“前几年我是不赞成设置临时摆卖的,但是如果不设临时摆卖就更加难管。”彼时,政府在广州各区都画了试点要搞“走鬼进商铺”,月租金600,就可以让走鬼们有一片安定的“揾食”场所。
走鬼不走了还能叫走鬼吗?果然,计划一流出,就在贴吧被网友大喷“天方夜谭”:“走鬼都是哪里人多去哪里,政府选的地方又远又偏,傻的才去。
2010年8月21日,广州召开走鬼问计会,管理部门跟走鬼又一次畅所欲言,试图“招安”走鬼。会议气氛很热烈,建议提了不少,又是搞特色街,又是借鉴新加坡推动走鬼合法化。
但到了亚运真正要开时,许多想法都仍是一纸空谈,走鬼问题依旧猖獗。
有走鬼在百度知道提问:“亚运会下个月开始,走鬼还能摆摊吗?”一位资深走鬼回帖传授经验:“可以,卖些小国旗就很不错。”
城管部门不高兴了,组织了9000多人,对全市100多个走鬼黑点“微笑执法”,又新画了200多个禁区重兵把守,几乎遍布市区繁华处。
一些走鬼选择回家避风头,还有一些则依然在地铁口、天桥底、城中村里与城管周旋。
就这样,城管与走鬼追追赶赶,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一片手忙脚乱之中度过了亚运。
没有伤亡事件的发生,倒是让各部门的一把手们松了口气。
05
亚运结束后,广州终于创文成功了,不是昙花一现,而从2011年开始,连续3届蝉联。
广州城管局曾经总结过后亚运时代的广州走鬼特点:“有团伙倾向,要防范乱摆卖演变成治安问题的可能性。”
但跟上一个10年,或上上一个10年相比,跟走鬼相关的治安问题或流血事件在21世纪10年代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唯一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大概是2013年广州城管向“走鬼”全面宣战时,白云山西门的一个场景:被没收了“家当”的走鬼抱怨:“没有事先通知,一出现就收缴物品。”城管局的一个副处长则回应:“难道我们每次来都通知你一声?”
2013年一轮清理,2017年为了迎接广州财富论坛又是一轮清理。
不知不觉中,排队也未必吃得到的阿婆牛杂就变成了连锁店;风筒辉、炒螺明从“街头霸王”,变成了只在纪录片里偶尔露脸的江湖传说;那些总在夜晚出现在二横路街边的烧烤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消失了……
当走鬼食摊都在广州的街头难以为继时,那些卖衣服的、卖首饰的、祖传贴膜的走鬼地摊们,就更别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了。
这当然跟每三年就要来一次的“创建文明城市”有关,跟城管部门坚持不懈地努力有关,但真正让走鬼走向消亡的,却并不只是权力。
亚运后的广州,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是深层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大家钱多了,即便是钱没多,无论从吃的还是穿的都已经“消费升级”,看不上那些地摊货了。再穷,也还有满大街的名创优品、10元店不是。
除了城中村或地下通道里,还有一些烧烤摊、卖红薯的骑着三轮车出动,或者某个天桥上偶尔有一两个卖袜子、卖指甲剪的,你很难再看到走鬼的身影。
唯一让人觉得还能支撑“走鬼”继续存在一百年的,只剩那句:
“蟑螂药,蚂蚁药,老鼠药,臭虫药,粘鼠胶,臭脚克星……”

06
接近40年前,作为返城知青大军一员的容志仁说:我也没有媒体说得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在求生存过程中,客观上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说老实话初衷就是为了生存。
历史又走到了相似的十字路口。
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失业职工数量创新高,847万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安置,还有千万级的农民工需要谋生。
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宣布: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列为今年创文考核内容。
许多人为此欢呼,为政府部门的英明决策鼓掌。
但这还是地摊经济的时代吗?
很疑惑,如果我失业了,我到底应该选择在朋友圈卖面膜呢,还是应该选择推个三轮车去地下通道摆摊呢?
要是摆摊,我应该卖红薯,还是卖老鼠药、蟑螂药、臭脚克星?
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了、经济恢复了,我还能和城管愉快地做朋友吗?
参考资料
1、《街边仔的酸甜苦辣》朱达成
2、《广州街头看走鬼》杨湛
3、《何不来个出租夜晚经营权》杨建燎
4、《广州开城管走鬼座谈会 商贩代表未语泪先流》新快报
5、《广州城管”走鬼”摩擦加剧 几乎每天都有城管受伤》羊城晚报
6、《关注广州走鬼现象》信息时报
7、《60瞬间·广州往事》
8、《广州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小女孩一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南方都市报
撰文 | JASON
编辑 | P.K
© THE END
图片源于网络
本文由识广原创出品,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互动话题
你还会买地摊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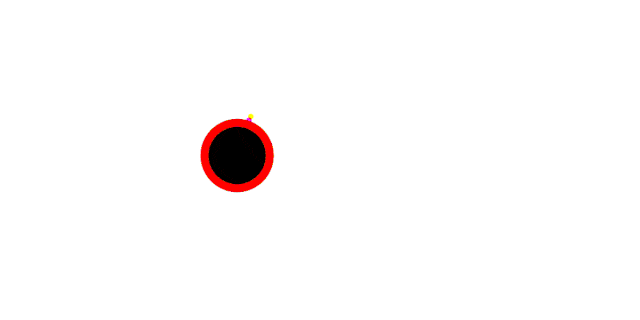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