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岁之前不会烫衣。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八年之久,几乎洗水衣衫裤不外乎穿竹穿肉,有一件半件“饮衫”,拿去洗衣铺洗熨好,有大喜事穿一次又挂几个月,这样的日子到了五十岁之后,和熨斗居然又结缘起来。这次倒是为了外孙而实践的,他的小衣裤袜枕套楼被尿布,经旋转烘干机出来,十足一堆“咸菜干”,为了 BB 的舒适,我用熨斗把它们一一侍候平展,就逐渐学会了用熨斗。


上世纪 50 年代,我恰齿之龄,家母是执教鞭的老师。她是苦孩子出身,历尽艰辛才争取到读书的好机会。恩师把家母当成自己的女儿般接待同住同吃,家母就替恩师洗熨衣服买早点夜宵报答她的知遇之恩。
我外婆守寡,到大户人家帮佣,学会一手烹饪和洗熨的好手艺。我小时候看着外婆和家母隔两三天就熨衣服一次,拆了床板搭起工作怡,形状似鸭子的黑笨铁熨斗,肚子装满木炭,烟腾腾二十分钟后炭火旺了,家母就把她的长衫斜布裤,斜布列宁装,大衣……熨得平整界限分明,每日每月都形象整洁站在讲台上讲课。那“铁鸭子会儿加炭,一会儿扇火,又要把水喷匀,又要铺上毛巾熨呢绒料。外婆和家母手脚不停,配合分工一丝不苟。等“铁鸭子”肚里的炭变灰色的“火尾”时,争分夺秒再熨一大堆小弟用的尿布围裙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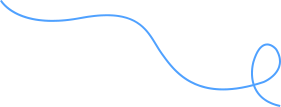
烧炭的老熨斗
这场大戏一般 10 点前停不下“锣鼓”。我困得东倒西歪,等她们拆下“戏台”铺回睡觉用的床,我就不辨东西爬上去睡沉了。
那只“铁鸭子”到第二天放凉透了,外婆把炭灰倒掉,擦干净包好放到我们小孩摸不到的地方上去,无论是热是凉,小孩从不准靠近和触摸它,以防意外受伤,从小我都对熨斗充满好奇和敬畏,又很烦要熨衣服的“大阵仗”。
时间到了 60-70 年代,生活方式远离斯文进入大老粗吃香时代衣服早就不熨也无法熨,木炭成了买不起的奢侈品,每个月配给 10斤木柴生煤炉。外婆当家每天买菜途中捡雪条棍和街上别人丢弃的小木块帮补着生煤炉。那时马路边种的树,有枯枝出现,人们争着勾下来拿回家生火用,有时争抢还惊动居委会出来仲裁哩。那年头夏天穿香云纱和的确凉(港澳亲友赠),那些衣服快干而不皱,冬天的衣服尽量折整齐用枕头压平,斯文屈服于穷困已渐行渐远,提倡革命化异变为全民大老粗,斯文受狙击继而被阉割,小资情调再无气候土壤。除了裁缝铺,熨斗“铁鸭子”从普通穷人家几乎下岗了。我家的“铁鸭子”不久就落入“收买佬”手中,换了许多盒火柴。
80年代中,电熨斗面世,裁缝们开始用了,而作为贵重的家电用品,大姑娘把它们列入嫁妆之中。那时的亲友们年节前会向有电慰斗的亲戚借用一下,于是不时有触电伤人的负面新闻让街坊们谈论起来。稀罕之中带点无奈。90 年代电熨斗已经普及,生活方式又开始追求美丽休闲。我两个成年女儿靓衫两大柜,她们熟练地各买了熨斗有空就打理那些靓衫。我由于对这工具从未接触,我乐得事不关己。
50 岁之后,外孙的衣物都是全棉的,我学着用熨斗打理那些皱巴巴的“咸菜干”,渐渐学会了这门久违的生活技能。如今慰斗,小巧安全,从有绳到无绳,熨板亦小巧收放自如,我把家里其他人的全棉T恤,学校制服,随时熨得平展整洁,脑中不时浮现起小时候等床板卸下来重整床铺才能睡觉的情景,百感交集,百味在心头。也很想念那古董“铁鸭子”木炭熨斗,很后悔当年眼睁睁看着他三不值俩地换成火柴。
特写下来与同龄老人家们分享。

当年屁也不屁的“铁鸭子”“铁尿壶”,如今觉得亲切且矜贵,蒙尘和铁锈也不让人讨厌它。
(图片来自网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