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或者是现在。
当芯片探索迈入无人区,AI持续加速摩尔效应,“硬科技”在全球科技竞赛中成为影响深远的决胜一子。
如果说,26年前首届高交会在深圳启幕,宣告深圳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引擎,书写“世界硬件第一城”的传奇。
那么,2024年湾芯展的举办,则意味着深圳不再满足于应用创新,而是向材料、设备、核心器件等从0到1人迹罕至的创新区域纵深挺进。
在这场关乎未来20年全球科技领导权的攻坚战中,遍布南山、龙岗、宝安、光明、龙华、坪山的“科兴企业家”仿佛是一个独特的标签,点亮起“硬科技”从设计到生产的不同环节。他们在优渥的产业生态中快速生长,同时又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建构者,反哺并塑造着深圳的产业生态。

南山科兴科学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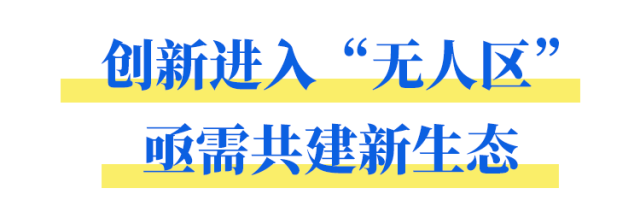
如今的企业竞争,不再单纯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区域产业链的竞争,甚至是城市产业生态的竞争。
当深圳“硬科技”的传奇篇章,正从 “集成应用” 的黄金时代,驶向 “自主可控” 的星辰大海,企业创新从1到100向前迁移到从0到1,对产业生态的需求较之此前更迫切、更丰富,也更深入。
深圳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成功的缩影。
如果没有1999年支持比亚迪在葵冲建立首个工业园,2007年329天完成112万平厂房建设,落地坪山;2009年将新能源汽车列入《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重点产业;2010年,创新“融资租赁”方式,鼓励巴士集团购买电动公交,2011年大运会采用电动出租和公交,2017年深圳全市公交电动化;2022年发布中国首部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法规,就不会有2024年深圳成为中国“超充之城”,2025年第1000万辆比亚迪系新能源汽车在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下线,也可能不会有欣旺达、贝特瑞、新宙邦、汇川技术、蓝海华腾、元戎启行、科陆电子、速腾聚创、格林美、英威腾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快速崛起,以及对深圳出口多年来的有力支撑。
要想种出参天大树,就需要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气候、肥料,以及足够和耐心。以芯片为代表的新一代“硬科技”尤为如此。
从1958年第一颗芯片诞生,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由于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创新起源多来自企业和实验室,但真正成功迈入爆发阶段的“硬科技”产业,从来都经历过漫长、多维和深入的产业保育。
城市能在多大半径内强化贯通产业链,在垂直链条上整合到怎样的产业要素,很多时候往往决定着能在多上游的环节实现创新突破,打造出自主可控的硬科技“热带雨林”,也决定着城市能否顺利跃入下一个黄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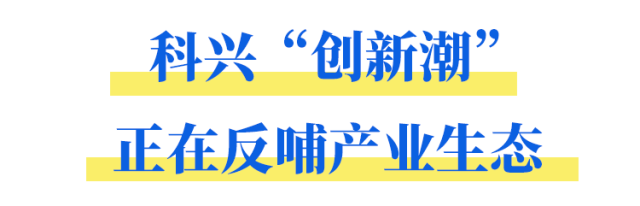
飓风穿过森林,掉落的树叶和果实,成就着森林沉寂百年的肥沃。
土壤决定了生物区系,但生物本身也在影响着土壤。
在硬科技的诸多产业环节,科兴企业家们正以 “破局者” 的姿态打破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可控,甚至引领创新。
在创益科兴科学园的实验室里,谷东智能创始人崔海涛兴奋介绍,近两年材料取得的重大突破,已经让产品效果日新月异。
大约一周前,谷东智能与合作伙伴联合推出三款AR终端产品及多款核心光学模组,新品涵盖企业级、消费级和专业户外场景。近期,谷东智能在二维全彩阵列光波导及PVG体全息光波导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创新突破。他预计,按照现在产品迭代的速度,到2027年AR眼镜将会迎来性价比趋于完美的成熟产品,正式进入千家万户。
谷东智能是聚焦新一代光波导技术制造商,最早光刻胶材料主要依赖进口,价格约4000元/克,等待周期动辄6-8个月。直到2019年,原有材料出现实验瓶颈,崔海涛意识到产品突破必须从材料突破入手。“当时公司分歧也很大,毕竟基于原有材料已经积累了大量算法和实验数据,一旦更换,前期研发积累相当于清零。后来研发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原有材料体系推进,另一组尝试开发新材料。”他说,中间也经历过长达半年的至暗时刻,原有材料想放弃,新材料却又看不到成果,好在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是2020年12月,那天终于看到光栅清晰成像,我当时心想,可以过个好年了。”
五年过去,自研材料、自研光波导模组、适配专业场景的AI算法,全栈自主可控给谷东智能带来供不应求的市场,产能扩张成为现在摆在崔海涛面前的幸福挑战。
“这是企业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没有人敢说自己能看准哪个技术方向,都是要探索、实验,螺旋式的上升。”崔海涛觉得,事实证明,原有材料的研发经验也并没有清零,材料、工艺、仿真,三位一体的研发路径,也成为后来创新的基础。
在南山科兴科学园里,摩尔线程研发团队也在挑战GPU的“不可能三角”——性能、功耗与成本的极致平衡。公开资料显示,创始人张建中曾在英伟达任职14年,为原英伟达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2023 年摩尔线程发布的 MTT S80 显卡,是国内首款支持光线追踪的消费级 GPU,性能达到同期国际主流产品的 80%,打破了海外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今年10月30日,摩尔线程获批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准备迁入光明科兴科学园的矩形科技,啃下至今仍被外资巨头长期占据,被称为工业控制领域明珠的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硬骨头”。创始人王晟磊不甘心“高端市场外资垄断,中低端市场国货内卷”的现状,以“航天级”工控产品起步,实现高铁、电力、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自动化的自主可控。

光明科兴科学园效果图
同方科兴科学园,AGI 企业云知声以600亿参数规模的自研“山海”大模型,在语言理解、医疗诊断等领域展现国内第一梯队实力,是首批将深度学习算法应用于商业语音识别的公司之一,也是国内AGI(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行者。今年6月30日,在港交所正式挂牌。

同方科兴科学园
从最初的材料创新,到终端的数据服务,再加上众多如未来穿戴 SKG、拥有160年历史智能门禁及安全解决方案全球前三的多玛凯拔这样的终端应用,在科兴科学园体系内,逐步沉淀出完整的“硬科技”产业生态。这也让科兴科学园,成为国内外“硬科技”明星企业来深“扎堆”的首选之地。
十五届全运会深圳站“0号”火炬手,也是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上一跑成名“小孩哥”的乐聚机器人在这里。
首家入选哈佛大学创新实验的中国团队,聚焦脑机接口,直奔机器人智能归宿的杭州“六小龙”强脑科技在这里。
硬核越野“坦克三兄弟”所属品牌,长城汽车也将华南区研发总部也在这里。
还有聚焦工业打印的全球独角兽Formlab 3D打印、美国芯片头部企业镁可微波技术等海外“硬科技”企业也将中国的研发中心,设立在科兴科学园。
创新的集聚,就像是一片浪花,吸引另一片浪花。他们或在深圳生长,或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共同掀起面向未来的“硬科技”浪潮,推动科技滚滚向前。
若换个视角,这些快速奔跑着的创新企业,不仅为产业生态补上弥足珍贵的一片,更反哺着科兴的产业生态,为生态注入无尽的勃勃生机,成为科兴科学园“自由奔放,活力科创”最有力的诠释者和定义者。
他们也似一片片拼图,共同铺就深圳这座科创先锋城市,快速发展最需要的城市底色。
城市保育了企业,企业也在长达十年,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默默塑造着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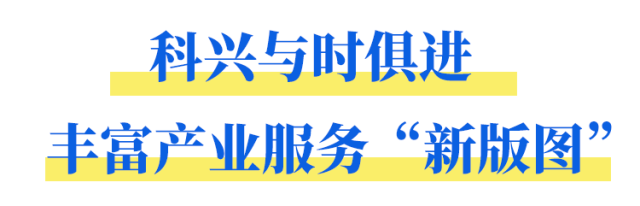
最聪明的企业,为什么总是选择科兴科学园?
产业生态是首要因素。生态的门槛是规模,即便放在大湾区,能够迈过百万平方米规模门槛的园区也并不多见。
没有足够丰富的物种,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物种之间的共生便无从谈起。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曾经说起,越是复杂的生态,形成需要时间越久,也越稳定。
科兴科学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拥有300万㎡城市科创空间运营经验。仅深圳一城,便布局南山、龙岗、宝安、龙华、光明、坪山六区,更在东莞滨海湾新区规划建设滨海湾科兴科学园,与深圳深度协同。

南山科兴科学园
年内即将开通的13号线,是被寄予厚望的深圳科创线,串联起深圳湾口岸、后海总部基地、南山高新园、西丽国际科教城、光明科学城,也串联起5个科兴科学园。
位于13号线高新中站的南山科兴科学园,出站直达园区;旁边的澳特科兴和创益科兴,也同样享受到13号线的便利;光明科兴科学园,距离6号线长圳站约400米,一站换乘13号线,半小时抵达南山科兴科学园,45分钟到口岸,尽享湾区顶级科创资源。
创建伊始,科兴科学园便致力于服务好深圳战略产业,为深圳培育小企业,留住中企业,引入大企业。
深耕科创产业园区至今,科兴科学园吸引超过1300家高科技企业入驻,其中包括超50家上市公司和5家独角兽企业。园区企业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高达5000件,拥有超过22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度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各个园区聚集了10万名高科技人才。
在科兴科学园内部,也已形成涵盖硬件研发、工控产线、生产制造、大模型、终端应用在内的完整“硬科技”生态。
近期,南山科兴科学园再次为产业生态集聚拿出诚意。非南山区数字经济企业入驻园区“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可申请最高30%的租金补贴,为意向落户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其次是空间。服务过足够多数量和类型的企业,经历过足够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才有可能会比企业家能更清楚地预见,企业即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才有可能提供真正适配的空间。
以创益科兴科学园为例,尽管地处南山粤海街道核心区域,堪称寸土寸金,依然特意为创新型企业配套中试空间,兼顾企业快速迭代研发和高知人群对生活质量的双重需求。
光明、龙华的园区,则更加关注企业研发、制造以及测试的系统需求,无论是人物动线、电网保障,抑或是楼层承重、货运物流,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很多企业家看过很多园区,最终还是选择了科兴科学园。
主打制造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同时开发一些机器人设备的蓝际工业,去年迁入光明龙邦科兴科学园。创始人袁军曾表示,团队工程师占比高,他更希望能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体验和愉悦感,让员工告别 “脑力农民工” 状态,因此选择了兼具厂房功能,但却更像写字楼的龙邦科兴科学园。
最后是服务。“财税人”公共服务平台、投融资对接会、周末社群活动,已经成为产业服务必备的三大例牌。
与其他园区不同的是,科兴科学园始终以“人”为原点,用社群思维做产业服务,构建了“8+7+6”产业生态圈,涵盖8大科创交流圈、7大活力社群和6大产业资源库,每年举办逾50场“筑企计划”系列品牌活动,帮助企业链接所需资源,在园区内把生意做大做强,让企业家可以聚焦发展,专注创新。
当硅谷回归硅巷,当创新企业从心无旁骛的郊区车库,迁往闹中取静的都市中心时,所有产业服务者就应该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新一代创业者,还是新一代企业员工,90后的学识和眼界,让他们在职业选择和城市选择上,都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服务,就变得极其重要。
只要看看多少科技园的年轻人,中午会去附近的科兴科学园吃午饭,看看多少加班之后的程序员,晚上不再睡实验室,而是睡在园区的公寓或酒店,就知道散落在各个园区的科兴天地商业,为什么成为科兴科学园品牌不可或缺的第四个支柱。
服务企业,不再止步于服务创新,服务制造,服务生意,更是服务好企业家和他的家人,服务好企业每一位无可替代的核心员工。
所以,当一家硬科技企业选择落户科兴科学园,它将得到的,不仅是量身定制般合用的半层办公或一层研发、生产空间,而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可以兼顾的平衡承诺,一张通往完整产业生态的长期入场券,一位陪伴企业全生命周期共同成长的伙伴。
科兴科学园一直致力成为中国科创产业园区第一品牌,相信科兴企业家们也终将和深圳共同迈入“硬科技”的黄金时代,共同打造全球“硬科技第一城”。
转载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作者:南方日报,来源:https://static.nfnews.com/content/202511/13/c11907322.html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