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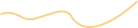
1977年下半年,高考恢复了。
其时我已厌倦了农场的生活,渴望有一个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我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个人表现非常勉强,与农场领导的关系相当一般甚至不太美妙,因此,我没有任何门可走。我连前门都没有,何况后门?让人心灰意冷的是,场长有一次放出风声了,说他不走,这画画的小子也别想离开从化。所以,命中注定,我只能走“捷径”,那就是高考。
四年农场,主要工作是出墙报,曾经画过几张大幅宣传画。在农场走得最密的是几个画友,整天廝混在一起,提着小画箱,到处寻找类似俄罗斯巡回画派列维坦那种阔大的风景。可惜眼前只有泥泞小路,以及山丘上密密麻麻的茶树和高大的影树。我们经常顶着暴烈的阳光,认真地在硬卡纸上涂抹着可怜的颜料,边琢磨技法,边把眼前土得掉渣的景色想象成天际线下辽阔的大自然。
我的目标是: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
当年全国的美术学院,最厉害的一定是油画系,叫“油老大”。所以,最难考的也一定是油画,其次是国画,再其次是雕塑。画画不行的人,只好委屈,去考工艺装璜。
报名的方式是,寄一张油画习作,如果通过,则可以拿到准考证,去广州美院指定的考场参加考试。我幸运,很快就拿到了准考证,兴高采烈地回到广州。我记得考场上有很多人。关键是,见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江湖大佬,他们画名远扬,让我辈敬畏不已。和他们竞争,几乎没有胜算。
一位在1977年已经名声大得吓人的青年画家,有过参加全国美展的经历,笑着对我们说,广州美院不行,他要明年去考中央美院。我一听,高兴得差点晕倒,因为这意味着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位也在画界具备某种社会名声的聪明人,现场指导我画静物,说,几个不同的橙子,前面暖一点,加点红色,后面冷一点,加点绿色,区别就出来了,既有色调,又前后关系,且很丰富。我一听就打内心里佩服,暗自下决心,考静物时就按这方法来描绘。还有一位,一看他表情,就知道已然成竹在胸,讲话口气大得吓人。
考题由各学院自行拟订。语文是当场写一篇叙事文,题目: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
写叙事文是我的拿手好戏。家教原因,中学时就熟悉杨朔和秦牧的散文模式,用这模式套革命题目,八九不离十。

图源:网络
我写了三场菊花会,当然是陪着从事文学创作的父亲去的。第一场发生在文革前,第二场发生在七十年代中,第三场发生在最近。第一场菊花绽放,第二场菊花凋零,第三场重新盛开,喻示着国家命运的巨大变化。居然,我的成绩是满分,至今还是广州美院文科考试的天花板。我想,作文怎么可能会有满分!?
开学后第一堂文学欣赏课,我见到了给分的老师,他是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我称呼他为老师,他摆手说:不要叫我老师,你是我的文友!你满分,是我给的。然后,我们就成了文友。闲时聊天,他总在讲没有实现的文学梦。他有时会不无惊恐地说,幸亏没当成作家,否则一定会给打倒。他说,如果不是文学梦,怎么可能在刚一解放时就从香港跑过来?等到明白一切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回去了。
一年不到,我的文友就离开了。他回到出生地香港,从此便杳无音讯。我一直怀念这位谦逊、有趣、从香港回归祖国参加建设、又在改革之初毅然离开的文学老师。
色彩考试是静物,画橙子。我用聪明人的方法,既保持色调统一,又力争色彩丰富。素描考试是头像,画女青年。我之前在农场已经画了无数张类似的素描,多少掌握了一些方法。创作则是勾一张草图,考的是主题创作的能力。我记得苏联人画过一张油画,描绘希特勒覆亡前在地下室的挣扎。于是,记忆加想象,我画了想象中的“四人帮”覆灭前夜的绝望情景,昏暗灯光下,四个阴谋家正在紧张地搞阴谋。
等候结果的时候最无聊,也最紧张,每天无精打采,既渴望成功,又准备失败。
一旦失败,我决定不再做艺术,而是去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一个作家!
历史真会开玩笑。很多年以后,我居然成为中大的一名教授。
我是农场第五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前四个都是外省高校,然后是我这一类的专科学院。看着眼前的录取通知书,紧张的心情一下子便放松了。晚上,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宿舍,跑到附近一个湖边,对着夜空高声嚎叫。夜空辽阔,杳无回音。
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广州了!
新生活马上开始。这一回可是艺术的生活,而不是别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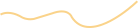
等我了解到招生的情况后,内心不免有所吃惊。聪明人没有考上!口气很大的也没考上。不屑于考广州美院油画系的那个江湖大佬,第二年去考中央美院,失败,第三年只好回头来考广美油画系,成了我的师弟。
不过,客观来说,他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有着独特的人生,只是,今天无人能识而已。
因为,他疯了。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个展览现场碰见早就不再从事绘画的他。他已过了中年,满头蓬松的头发,身材瘦小结实。我照例和他打招呼,他马上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声点,有人在追杀我!我给吓着了,连忙问:有仇人?他不无得意地笑着说:当然,是中情局的人!我听不明白,中情局会理睬你这个广州街头一事无成的艺术家?他看着我,表情更加神秘,低声说:我发明了一个水变油的技术,非常靠谱,石油垄断将会成为过去。你说,能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霸权!我掌握了如此厉害的技术,中情局的人能不来追杀吗?他们背后站着的可是石油财团呀!他们马上就要破产了,真的怕了!
我盯着他的脸,发现他说话时特别坦然,特别正常。
我把这事告诉我的另一个朋友,颇为狐疑地问:他是否有点神经不正常?朋友果断地说:什么不正常,他已经疯了!
哦,疯了!
更可怕的消息是,外间传说,这一次考广美油画系的,其中一人考前已参加了三次全国性的油画展,而广美油画系的众多老师中,有几个一直都无缘于全国大展。所以,这一次招生,与其说考学生,不如说考老师。

下:民乐茶场的茶山

杨小彦 画
上图是1976年的纸本油画(自注第一次画出的阳光感)
下图是1978年入大学前的油画作品
的确,我们班里是有这样一位人物,考前已参加了三次全国性的油画展,其中一张还给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今天成了社会名人,过着名人的正常生活,在一家以他命名的美术馆做馆长,每天忙于馆务,以及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被簇拥、被签名、被合影、被追捧。
他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勤奋,这源于入世;因为入世,所以必然勤奋。况且出生苦难,没有想入非非的资格,每走一步,都不能闪失;每一次机会,都必须牢牢抓住,丝毫不能放松。很多年以后,他出自传,感谢一路走过来相助的贵人。同学们自然都获得了赠品。我翻开认真阅读,很快发现,书中所配图片,说明中凡出现人名的,一定伴随显赫的职务;如果没有职务,则一律称为“老同学”或者“老师”。我有点传播学的常识,知道这叫“议程设置”,意图优先,是一种刻意的设计与编排。
成功者都不容易。成功者只讲成功,可以理解。
班里真正的才子却一直都不出名。或许才子意味着自负,无视世俗名声。还有就是,我们这一辈人,总怀揣着一个出国的梦,以为到了外面,很快就会像安格尔、莫奈、马蒂斯、萨金特那般闻名于世。殊不知出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比里头的世界还要实际,实际到了,每天最重要的就是三顿饭钱的来路。想起电影《金山大道》里一句有名的台词:“没有肚皮,那顾得上脸皮?”脸皮属于艺术,肚皮属于生存。没有生存,哪来的艺术?
我发现,几乎所有出国的人,他们的思想状态大致上都保留在出国时的水平。这边在飞速发展,变化速率快得不可思议,外面却稳定,多少年差不多。所以,内外差距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曾经是同学,但却越来越难以对话。渐渐的也就不来往了,因为不能来往。
其中的障碍是趣味,趣味具有在地性和时间性。待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人群,解决不同的生存困境,趣味怎么可能一致?趣味的麻烦还在于,这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交流的东西,一交流就会反目成仇。
何况,趣味没有错对之分。
不管怎样,我终于成为一名“油老大”,虽然在班里水平中等,才气不足,但走在昌岗路广美校园的小路上,昂首阔步还是经常的姿态。
很多年以后,我为我的老师徐坚白老人家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开幕式后,徐老师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喃喃说道:当年我觉得你和你们班的人都牙擦擦的呀(粤语狂妄的意思),怎么现在肯为我策划个人展览?我谦卑地说:徐老师,那个时候不懂事!
这就是“油老大”的结果。想来真是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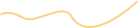
上课了。
老师各色各样,什么性格都有。艺术的神秘性全在课堂里,全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
一年级基础课是画石膏,老师强调其教学体系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背后是著名的“契斯恰科夫”体系。石膏画在素描纸上要位置适中,既不能出格,也不能太小。要注意结构,注意骨点,注意转折,不能含糊,不能搞效果。最后一条非常重要,所谓搞效果,意思是,用手擦一下暗部,有个大效果就可以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我的作业的意见很具体:所画石膏没有质感。我问老师,如何才有质感?老师微笑着说:画的要敲得响呀!说完用手指敲了一下石膏,发出空洞的一声。
哦!要敲得响!
我愚笨,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敲得响”。问同学,同学说,大概分面要清晰吧。于是我把所有的石膏分面都画得清清楚楚,然后,又给批评说,画得太碎了,不整体。反正,怎么都不对。
重要的是,没有定义。
才子画石膏却很独特,从石膏翻模时留下来的痕迹开始画起,局部入手,局部完成。老师强烈地要求他改变画法,要从整体入手,渐次深入,像暗房里显影盘中的照片,缓慢呈现。可才子根本就不理睬,我行我素。最后作业完成,老师傻眼了:画得准确,而且,充满了让人惊讶的细节,比如石膏给弄脏了的表皮,居然一丝不苟地画了出来,效果全班第一。
才子的石膏不仅敲得响,而且还有触摸感。

通往落基山深处的路 杨小彦画(2011年)
改革初期,思想解放,学校恢复画女人体,从我们班开始,再推广到其他系。
鬼叫我们是“油老大”!
人体是纯然的审美,是训练审美的基础。不过,70年代末的广州很保守,找不到愿意做这一行的女模特。所以,第一个模特是从中央美院借过来的。
我们这一代人从紧张时期成长过来,从小知道男女受授不亲,盯女同学的脸多了可能会有麻烦,恭维一下美丽的女性一定会收获臭骂,“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性感”是下流黄色用语。学画时,听说70年代中有人大胆地在家画女人体,给抓了起来,公开宣判后毙掉了。70年代末,广东有个雕塑家为纪念可怜的张志新,把烈士做成女裸体骑在马上飞奔,引起掀然大波。北京有一个先锋画家画首都机场壁画,题材是“泼水节”,画了几具裸体,结果给用布遮了起来,以免有伤风化。
这是一个可怕的禁区。
现在,终于可以合法地、公开地画女人体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人体课那天,老师把我们叫到外面等候,她在里头先行布置。然后,老师从教室门口探出头来,招呼我们进去。同学们鱼贯而入,默不作声。课室里画架一字排开,都是我们平时的位置,大家站在画架前,手握铅笔,注视着模特台。模特台上有一张椅子,背后铺上灰色的布。屋角临时搭了一个小空间,是模特换衣服的地方。老师冲着里头叫唤说,出来吧,开始了。于是模特披着睡衣走出来。她走到台前,双手轻轻一甩,衣服就丝溜地滑了下来,露出了匀称而洁白的身体,灵巧地摆好了优美的站姿。现场哑雀无声,只听到铅笔在纸上轻划的沙沙声。所有男生估计都一样,平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女裸体。完全无语。几个女生也保持着沉默,不知她们做何感想。很快,老师洪亮的声音嚷了起来:怎么形都画不准?要把人体恰当地摆进去,不能砍头,不能去脚!
这种略带紧张的气氛也就两个小时,就都放松了。窃语声随即泛滥,尤其是女生轻脆的吭唧,似乎在去掉某种异样的情绪。
要知道,下一张是画男人体。
一周下来,课堂上便有说有笑了。模特和我们混熟了,休息时不再回避,甚至连睡衣也不穿,光着身子在画架之间穿行,不时评价着我们的素描,说这张像,那张不好看,或者质疑这张把她画胖了,又嫌另外一张太过美化了。老师对同学们有过交待,说模特也是一种革命工作,是为艺术而献身,所以一定要尊重人家。于是,周末全班出去活动,上白云山玩,把模特也带上,让她和我们一起领略广州的风光。
广美一直到今天,男人体都带着一小兜,不是全裸。中央美院从一开始就男女全裸,其他美院也是如此。为什么如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当初的女生,她们不叫男的全裸,难道要我们去叫吗?
在美院,模特属于教具,归教具科管,一点也不“人性”,更无“艺术”。每天上课,班长到教具科去领教具,也就是去领模特,带着到课室来上课。模特习惯了,当众脱换衣服,自然而然。唯一让我们好奇的是教具科长,一个中年人,每有新的女模特到,他一定会出现在第一堂上,掏出小速写本,拿着铅笔,认真地对着模特作画。久之,我们明白,他这是要享受“初看权”。
画人体是一个高级的课题,不容易处理。而且,画久了,画多了,画出模式了,大概也就画不好了。到三年级时,我们觉得最无趣的课就是画人体。
2022年8月20日,广州祈福
发表于2023年第2期《随笔》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站立场。作者:杨小彦,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考大学及开学的若干片断》https://www.gznf.net/column/109067.html






评论